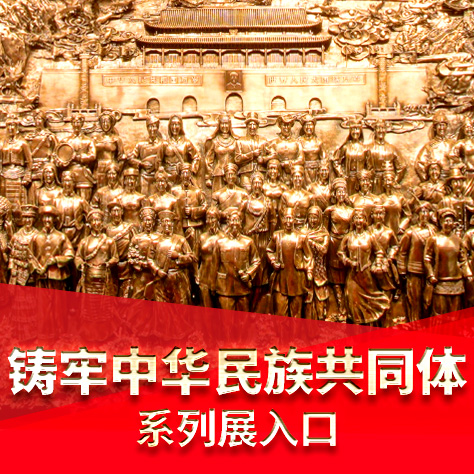新疆、西藏、蒙古位于清朝西部和北部的边疆地区,在清代被称为“藩部”,由理藩院管理,并以将军、都统、大臣驻守。《皇朝藩部要略》《蒙古游牧记》《清史稿·藩部传》等史籍对清代新疆、西藏、蒙古的情况有详细记述,有助于人们了解清代边疆历史特点,认识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性。
自古就属于中国且地位重要
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,地大物博,人口众多,民族多元一体,发展延续不断。尽管在发展变化过程中,发生过许多次朝代更替,但是,这些都是中国的内部变化,中国整体局面并没有受到根本影响,反而是在变化中有了新的发展。清代西部、北部边疆地区自古就属于中国,不同朝代都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。蒙古地区,在秦朝曾被九原郡管辖,在汉朝设立了使匈奴中郎将及安定等属国,在唐朝设立了安北都护府、单于都护府,在元朝有岭北行省,在明朝封蒙古首领为顺义王等。新疆地区,汉朝曾设立西域都护府等军政机构,唐朝设有安西都护府、北庭都护府,元朝设立北庭都护府以及阿力麻里元帅府等,明朝设有哈密卫及有关指挥佥事,以及封蒙古首领为顺宁王、贤义王、安乐王等。西藏地区,元朝设有帝师、宣政院以及吐蕃地区的都元帅府进行管辖,明朝设立乌斯藏都司、朵甘都司和诸法王。综上可见,清朝对新疆、西藏、蒙古的管理,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管理西部、北部边疆地区的延续和发展。
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,尤其表现在稳定政局方面。对清廷来说,既有历史经验,也有现实教训。历史经验就是明朝与瓦剌的关系,瓦剌是明朝人对西部蒙古的称呼。明成祖朱棣即皇帝位后,曾派使臣告谕瓦剌部。永乐六年(1408),瓦剌首领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贡马请封;永乐七年,明朝封马哈木、太平、把秃孛罗等首领分别为顺宁王、贤义王、安乐王。正统四年(1439),马哈木的孙子也先嗣王位后,瓦剌势力处于极盛期。正统十四年,也先大举攻明,宦官王振挟明英宗亲征,败于土木堡,明英宗被俘,被称为“土木堡之变”。随后,也先直犯京师,被于谦击退,只好与明讲和,送还英宗,致使明朝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清朝皇帝熟悉历史,不可能不知道这段故事。现实教训则是平定准噶尔部用了三代人几十年的时间。康熙年间至乾隆年间,准噶尔蒙古噶尔丹、策妄阿拉布坦、噶尔丹策凌以及阿睦尔撒纳等与清廷的和与战,带给清廷无限的烦扰,极大地影响了清廷统治秩序的稳定。乾隆皇帝认识到,不彻底解决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问题,蒙古地区就不会得到最后的安定,清廷在中原内地的统治也将受到影响。这正是他下决心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根本原因。
民族和宗教特点显著
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的主要民族是蒙古族、藏族和维吾尔族等,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。在归附清朝以前,蒙古族正经历封建领主制发展阶段,其居住地区形成的各部,就是规模不等的封建领主集团,拥有大小不一的封建领地。其中,牧户是基本经济单位,要提供赋税和兵役。在各封建领主之间,还存在着集会形式,用以调解彼此间的关系。各部蒙古族的社会经济以游牧畜牧业为主,打猎、捕鱼、手工业和其他副业为辅。有些地区,农业有了相应的发展,与中原等地的贸易水平也有了提高。各部封建领主之间不断发生战争,社会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坏。归附清朝以前,西藏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,官家、寺院、贵族形成三大领主,属于社会上层,是统治阶级,属民则成为社会下层,是被奴役者,也是主要生产者。农业、畜牧业和手工业是藏族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,此外,与云南、陕西、甘肃等地也有贸易往来。
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,维吾尔族在维护国家统一、反对外来侵略和民族分裂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,产生了许多杰出人物。在归附清朝以前,维吾尔族社会是世袭封建主统治的社会,实行世袭的伯克制度。各级大小不同的世袭伯克,就是大小不同的封建领主,其中汗的地位最高。经济上,维吾尔族社会以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基础,生产者就是受各级大小不同的世袭伯克剥削和压迫的属民。维吾尔族在农业、采矿、冶金和手工业方面都有所发展,与内地的贸易也很密切。由上可见,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多是少数民族居住区,在社会制度、生产方式、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各有其特点。
清代西部和北部少数民族居住区的主要宗教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。7世纪,佛教传入吐蕃,与当地苯教相互影响,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,并一度兴盛。9世纪中叶,当地统治者兴苯灭佛,藏传佛教受到限制。10世纪后期,藏传佛教再次得到发展,形成许多派别。13世纪后期,在元朝扶持下,上层喇嘛开始掌握西藏地方政权。15世纪初,宗喀巴进行改革,创立格鲁派,亦称黄教派,在西藏逐渐得势。这是藏传佛教在西藏发展变化的大致情况。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有一个过程。先是蒙古族贵族在对西北用兵过程中,接触到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,即红教。后来,由于元世祖忽必烈的推崇,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族上层贵族中传播。16世纪末叶,黄教派传入蒙古,首先在漠南蒙古传播,归化城的伊克召(弘慈寺)、席力图召(延寿寺)、美岱召(寿灵寺)等寺庙相继修建,成为喇嘛僧布教活动的场所。随后,喀尔喀蒙古也开始信仰藏传佛教,明万历十七年(1589),喀尔喀蒙古建立额尔德尼召(光显寺),延请大活佛前往讲法。藏传佛教传入漠西蒙古的时间要稍晚一些。明万历四十三年,栋科尔满珠习礼胡图克图以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代表的身份,来到漠西蒙古,劝说和硕特部封建领主拜巴噶斯等皈依藏传佛教。从此,藏传佛教在漠西蒙古传播开来。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我国蒙古族各部广泛传播,不是偶然的,这既是蒙古族封建领主政治上的需要,又是广大牧奴精神上的需要。伊斯兰教在中国旧称回教、天方教、清真教等,7世纪传入中国。伊斯兰教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,传入中国的主要是逊尼派。西域的维吾尔族等信仰伊斯兰教。从以上可以看出,藏族、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,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。全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,这在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是一大特色。
与内地有密切联系
从历史上看,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,在经济、文化等领域与内地联系密切。汉朝开辟和维护了中原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,被称为“丝绸之路”。通过丝绸之路,中原内地的丝绸输入西域,促进了西域毛织水平的提高。中原内地的铸铁技术、制陶技术、制漆器技术、穿井技术也传到了西域,促进了西域生产技术的发展。纸张也开始在西域使用,中原文化对西域产生了影响。西域的一些农作物和乐器传到了内地,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。特别要指出的是,佛教正是在汉朝通过西域传到中原内地的。在唐朝,西域和中原内地的关系更为密切。西域各少数民族有许多人留居长安(今陕西西安),为中原内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随着内地和西域人们往来的加强,内地开始使用西域的造酒技术,西域的音乐也传入内地。元朝修建了连接西北边疆和中原内地的驿路和驿站,使两地的商业往来日益增多。畏兀儿商人把当地的特产运到内地,再把内地的商品运到西北地区,促进了两地的商业繁荣。内地的农耕技术、雕版印刷术传到了西北地区,提高了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。在元朝,吐蕃地区和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了发展。吐蕃地区的建筑、美术、工艺等被介绍到中原内地,内地的雕版印刷术传到吐蕃地区,促进了吐蕃文化的发展。在明朝,许多西域商人往来内地,有的在京商贩,留住三四年之久;有的沿途寄住,贩物谋利,经年不归。通过贡使和商人的活动,西域的良马、玉石以及各种鼠皮运往内地,内地的粮食、茶叶、纱罗、棉布、瓷器、纸张等运往西域。蒙古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很频繁。中原内地的药物、纸张、书籍通过各种途径传到蒙古地区。西藏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得到发展。一些乌斯藏僧人将藏传佛教及佛教艺术传入内地,又把内地的文化及纸张传入西藏,促进了西藏佛教典籍和文学、史学著作的刊行。
进入清代以后,蒙古、西域、西藏都和中原内地有经济文化交流。顺治十二年(1655),清廷允许喀尔喀蒙古八扎萨克,每年进贡白驼一、白马八,照例各赏给银茶桶、茶盆、蟒缎、缎布等物。顺治十三年,清廷决定,厄鲁忒达赖汗使人返还,给驿马25匹、马车12辆。其带来马驼,每宿处给与草料,至西宁止。顺治十八年,清廷又决定,厄鲁忒来贡者,途中买来喀尔喀男妇子女,准其转卖,令买主于户部存案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清廷决定,厄鲁忒噶尔丹进贡使臣,有印凭者,许进内;其噶尔玛等四台吉使人,无印凭亦准进内。皆不得过200人,余者令在张家口、归化城贸易。西藏达赖喇嘛、班禅额尔德尼和内地的经济往来,清廷亦有明确规定,对达赖喇嘛多至数百人的来使,清廷也做出必要的安排。乾隆四年(1739),清廷更做出准噶尔和中原内地贸易的具体规定,于寅、午、戌年来京贸易,其子、辰、申年,令于肃州贸易。均由准噶尔地方,将货物起程日期,及何地可至边界之处,预先报知驻边大臣转奏,贸易事毕由原路送还。
综上可见,新疆、西藏、蒙古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,藏族、维吾尔族、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,西部、北部边疆地区与内地在历史上就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。因此,研究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历史特点,不仅要考虑到清朝的史事,还要了解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。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)